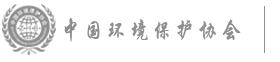图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科考船,用于声呐探测。
3000公里可以是一个人驾车从北京前往海南省三亚市的距离,也可以是一条中华鲟从大海出发回到故乡长江产卵的距离。如果不出意外,每到夏秋季,成熟的中华鲟会结伴而行,逆江而上,在长江中等待一年后,次年秋冬时节来到湖北宜昌葛洲坝下游江段的卵石滩繁衍生息。然而,作为长江的旗舰物种,2017年以来,科研机构已连续4年未在长江里监测到中华鲟的自然繁殖。
今年,中华鲟产卵场的调查工作还在继续,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于11月9日,在长江启动了为期两个半月的中华鲟产卵场科考调查活动。
一次次的科考调查活动,还原着中华鲟的生活习性与生存现状。如今,中华鲟的命运将走向何处,而它们又无言地诉说着长江生态的哪些秘密?
“没有监测到鱼卵也是一种调查结果,将为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阴雨天的早晨,江面笼罩着一层水汽。在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内,4艘调查工作船会按照各自的分工,开启一天的航程。它们分别通过渔业水声学调查、水下视频观测、中华鲟卵苗捕捞、食卵鱼解剖等手段,对中华鲟产卵繁殖情况进行调查。
“我主要负责食卵鱼的解剖工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段中华是调查工作组的一员,“每天,渔民带着我的同事在中华鲟产卵场附近打捞20公斤-25公斤食卵鱼,包括铜鱼、圆口铜鱼、瓦氏黄颡鱼等。根据对食卵鱼的解剖,就能推断中华鲟是否有自然产卵,以及产卵时间和产卵地点等。”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半个多月过去了,对所有食卵鱼的解剖都未发现有中华鲟鱼卵。同样,其他几方面监测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糟的?
个体硕大的中华鲟起源于白垩纪,在1.4亿年的进化历程中,自2013年首次出现产卵繁殖中断,接着2015年中断,2017年-2020年又连续中断。
农业农村部2015年印发的《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中也指出,中华鲟命运的恶化,与20世纪后期过度捕捞和环境退化(筑坝、水污染等)等人类活动的影响分不开。上世纪80年代,葛洲坝开始修建,原本要溯江而上到金沙江产卵的中华鲟,被迫留在坝下水域繁育后代。1983年,科考人员曾在坝下发现两个新产卵场。一年复一年,如今,葛洲坝至庙咀长约4千米的江段,是目前为止唯一已知的中华鲟产卵场。直到2020年,科考人员在这里监测到13条成年中华鲟,但并未发现自然繁殖现象。
“截至目前还没有监测到有鱼食卵现象,即没发现中华鲟产卵,不过这也是一种调查结果。”段中华告诉记者,“科考活动的最新数据可以为后期开展中华鲟群体补充和增殖放流工作提供参考。”除此之外,科考活动还将通过对繁殖群体数量、繁殖行为以及环境条件等多方面的监测结果,来综合分析中华鲟的生存现状,为下一步的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自然群体规模缩小,让自然繁殖难上加难
在长江上游孕育,在东海、黄海和渤海成长,成年后又千里迢迢归来,到出生地寻根、产卵,这是科考人员所还原的中华鲟的生活轨迹。而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加大,这一过程逐渐变得艰辛。2013年,中华鲟开始出现产卵繁殖中断。“我们分析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当时环境条件不太好,中华鲟产卵需要水温在20℃以下,但随着长江梯级水电工程的建设,秋冬季水温下降变慢。”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刘焕章告诉记者。
实际上,水库的滞温作用,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都让产卵期的水温发生了显著变化。相关数据显示,1980年至1983年、2002年至2005年、2013年间,中华鲟产卵期(10月至11月)的平均水温分别为16.2℃、17.8℃和23.8℃。水温陡然上升,导致稳定了近20年来的繁殖期向后推迟了一个月。
相关研究还表明,河床地形、河床质、流速场、自然繁殖季节的水文状况和气象状况都影响着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活动。而这些环境指标的不利变化,都有可能让中华鲟放弃产卵。
这几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好的转变。随着长江大保护战略的推进,尤其是今年以来,长江“十年禁渔”计划的实施,不仅给长江生态修复带来了良好契机,也给长江生物带来了改善生存环境的机会。
在葛洲坝至庙咀的江段,中华鲟产卵场如今还在,却难寻产卵迹象。“实际上我们分析,产卵场的环境条件应该是可以的,没有繁殖的原因,我们认为有可能是繁殖群体的规模太小了,也就是鱼的数量太少了。” 刘焕章表示。
事实上,自然群体规模的缩小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据研究人员估算,1970年代,中华鲟的繁殖群体数量在1万尾左右,1980年代约2000尾,1990年代约400尾,21世纪初则在200尾左右,2010年以后,资源量下降到不足百尾。这也导致中华鲟的生存陷入恶性循环:种群数量的减少导致繁殖可能性的降低,而自然繁殖可能性的降低将会导致种群进一步减少。这一结果是诸多因素叠加影响造成的。
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增殖放流依旧是主要保护手段
人们在保护中华鲟的过程中尝试了诸多方法。
1983年以来,累计放流至长江中的中华鲟鱼苗约有700万尾,其中50%是刚孵出的幼苗,这是一组看起来令人倍感欣慰的数据,然而实际情况却比想像的要复杂。
“如果没有放流足够大和足够多的个体,对于恢复自然繁殖的贡献就不大。”刘焕章解释,“这些放流到长江的中华鲟幼苗存活率较低,除了个体偏小,数量也偏少。一头成熟的中华鲟一次产卵可达100多万粒,人工增殖放流可能就几十万尾,在同样高的自然死亡率下,这跟自然繁殖的规模也是没法比较的。”然而贡献虽有限,但增殖放流也给中华鲟野外种群恢复提供了一些可能。
数量越多,希望才越大。今年10月28日,“农业农村部荆州中华鲟保护基地”在湖北荆州市中华鲟保护中心挂牌。农业农村部长江办力争通过3年时间,在这里建成高规格的中华鲟驯养繁育、野外驯化、增殖放流、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对外交流等六大基地。也有专家正在呼吁,实施国家级的中华鲟增殖放流和资源修复计划。
可喜的是,中华鲟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行动也正在开展。每年,科考人员都会在不同的季节来到长江开展有关中华鲟的监测活动,相关的监测和救护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野外种群自然繁殖的成功,才应该是中华鲟物种保护的最终目的。”刘焕章坦言,“虽然以现在的技术,人们仍能见到人工繁殖的中华鲟。不过,只有中华鲟能够野外繁殖,经受自然选择的考验,才能说是中华鲟物种保护的成功。”
大海是中华鲟成长的的重要场所,因为那里有它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食物,而长江是中华鲟繁衍的“摇篮”,期待中华鲟转危为安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