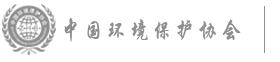|
|
位于三江源地区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境内的年保玉则风光。 |
155头牦牛,全卖了。
把旧物什塞满双排货车,又拉着阿爸阿妈,还有三个妹妹上了车,忍不住回望,沱沱河慢慢模糊在风雪中……24岁那场远徙,才是闹布桑周的成人礼。告别唐古拉、翻越昆仑山,年轻的牧民小伙放下牧鞭,忐忑间扛起全家的未来。格尔木城市南郊的移民新居,刻着故乡的根:长江源村。
那是2004年冬,青海省唐古拉山镇6个村的首批128户牧民自愿搬迁。故土难离,“心里可不好过了”,下山时,草场封牧的闹布桑周家,还顶着一个并不好听的“生态难民”帽。
而草原的“预警”来得更早。
“读小学时,夏天常和尕娃们下河扑腾,沿岸的河床都是枯的,水浅,长辈们也不用管。”成年后,桑周随着阿爸去放牧,看到遍地鼠洞,还有星星点点的草原“斑秃”。“光牦牛,唐古拉山镇最多时就畜养过7万多头。草不够吃了,有的畜牧大户,不得不跑到两百多公里外的昆仑山野牛沟游牧。”
同样焦急不已的,还有仁青多杰。
2004年,作为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机关里的年轻人,他三天两头下乡,眼瞅着由于长期过度放牧等因素,“全县七成的草地都退化了,而且还在走向沙化。不夸张地说,每平方米草地都寻不到几根草”。
素有“黄河之源千湖县”美誉的玛多,全县湖泊数量一度从4077个锐减到1800个。当“长江源头支流楚玛尔河断流”“黄河鄂陵湖出水口断流8公里”“澜沧江源第一县垃圾围城”之类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举国上下疾呼:救救三江源!
一场保护“中华水塔”的绝地反击,在广袤的青海高原上,很快拉开大幕:2005年,国家正式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开展人工干预、应急保护。
这是世界罕见的治理规模:在三江源地区的4个州17个县市,全面实施了水土保持、沙化治理、退牧还草、移民搬迁、湿地保护、人工增雨、工程灭鼠等22项工程1041个治理项目。
“玛多县对其中2511万亩退化草场全部封牧。”仁青多杰见证了黄河之源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按照牧民自愿原则,先后有585户2334人搬迁出生态保护核心区。”
住进移民新居明亮的砖瓦房,父母看病方便、三个妹妹就近上学,再不用受风吹雨淋的游牧之苦,还享受着按时发放的草原生态奖补,可闹布桑周没有躲在“舒适区”,一番摸爬滚打,牧民变成市民,“坐骑”也从摩托车换成了越野车。
阵痛总是暂时的。在长江源头流域面积最大的原始林区玛可河林场,从普通伐木工到林区管理者,粗粗壮壮的赫万成带着老伙计们“二次创业”,他这样总结自己在玛可河工作的三十载:“从森林砍伐者到生态保护者。给后代留下一片绿水青山。”
历经艰苦卓绝的努力,三江源迎来重生:一期工程实施十年后的2015年,三江源各类草地产草量提高了30%,百万亩黑土滩治理区植被覆盖度增加到80%以上;三江源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560个西湖;近十万牧民放下牧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4%。
也是在2015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作为首个试点,三江源正式开启了国家公园改革新时代。
仁青多杰有了新职务: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执法大队队长。国土执法、环境执法、草原监理、渔政执法等原先“政出多门”的监管工作,他如今“一肩挑”。
国家公园怎么建,青海敢于“吃螃蟹”: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其下组建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三个园区管委会,对所涉4县进行大部门制改革,将县级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分别整合,理顺了自然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关系,解决了执法监管“碎片化”的顽疾。
“总结起来,就是变‘九龙治水’为‘一龙管水’。”赫万成一语中的,如今担任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的他,正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督查和国家林草局的评估意见,忙着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年内正式设园。
改革在以点带面、走向深入。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经验为基础,青海省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的蓝图,正在全省范围徐徐铺开。
人努力,天帮忙。2019年,玛多县全县湖泊数已恢复到5050个。“千湖美景重现,而且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仁青多杰嘴角一扬。
已成为生态管护员的闹布桑周,每个月都坚持重回草原,监测草地载畜量、统计野生动植物种群状况……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有17211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园区全面实现了“一户一岗”。闹布桑周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记者倾吐初衷:“回去参与生态管护,为的是尽一份草原儿女的责任,让故乡多一份美丽。”
长河上下、一去一回,串联着三江源的历史、今天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