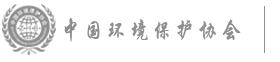作家陈应松
作为当代最著名的生态作家之一,陈应松的生态写作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一入深山二十余年,在神农架的生活与创作中,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支点,站定了自己的“森林立场”。在他的笔下,有对动物顽强生命力与生命尊严的歌颂,有强烈的反对生态乌托邦的现实主义色彩,有反思现代性、重建现代人精神家园的呼唤,有饱满的传统楚文化遗风和中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他用他深刻的生态书写,对人类与万物关系的深入思考,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界做出了独特贡献。评论家王春林曾说,“再也别想写森林了,至少三十年,你也写不过他了。”
本次对话中,陈应松向记者呈现了他对生态文学写作、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思考,展现了他在生态文学创作方面“越过高原攀高峰”的孜孜以求。同时,对话中他也首次披露自己写作时的一些方法、经验,尤其是他写作时的精神情怀,相信会让读者有所收获。
◆对于一个生态作家来说,不能为写生态而写生态。
◆你只有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实的世界,什么是真实的大自然,生态文学才有价值。
◆我喜欢自然山野,因为它们是文学的故乡,也是文字的舞台。
◆你写一头猛兽跟写一个病毒,在题材上面,它的意义是同等的。
◆上苍派我来人世就是写字的,写作跟我的呼吸融为了一体。
中国环境报:您曾经说过,作家是非常注重体验的,包括您自己的写作。请问,如果要写一部反映生态环保主题的作品,您会对哪个方面感兴趣?
陈应松: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喜好。我受到文坛认可的作品,就是神农架系列小说,我的写作对象是森林、动物,这是我感兴趣的领域。
生态作家所写的对象,有他自己想要表达的语言或者哲学观、生命观和世界观在其中,每个人的关注点是不同的。我喜欢写的动物,都是一些大型兽类,像豹子、熊、野猪,它们是地球上的灵兽,有神秘性、传奇性。神性的、神秘的色彩,可能更打动读者,在文学上的意义甚至可以上升到人类精神层面,它带给人和生命的启示是广阔的、深刻的、复杂的。
所以,我觉得生态作家还是要抓大不抓小,写就写那种神奇的、壮美的、具有英雄气质的动物、植物。从生态学观点来说,了解这样一些动物,对唤醒公众的生态意识是有巨大帮助的。
中国环境报:如今很多人关心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参与生态文学写作。我们也呼唤更多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出现。对此,您有何建议?
陈应松:一个好的生态作家,首先是一个好作家。生态,只不过是当前文学界或者时代召唤下大家的一种说法,其实生态作家跟所有作家一样,就是个作家。
对于一个生态作家来说,不能为写生态而写生态。首先,他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还要成为一个有自己精神向度、精神维度、精神坐标、精神高度的作家,他才能写出包括生态的作品。
一个作家倾情于某一种题材,某一种写作对象,也是他自己的喜好,是某种精神外化。他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只不过是借助了某一个动物,某一种植物,来倾吐他内心全部的精神渴望、梦想和追求,找到攀向某个高度的路径。
如果你渴望在作品当中有大悲悯,有神性,有神奇的力量或者英雄主义气质的话,你写的东西肯定跟其他作家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生态写作要提升它的品质和提升它的高度、提高它整个精神向度与境界,还是要老老实实地面对大自然的真理和真谛。
中国环境报:那在您看来,大自然的真谛是什么?
陈应松:就是真实的大自然,就是大自然的残酷性。大自然各种生物的生存法则,有它自身的规律,我们应该尊重它,才能书写它。
不能仅仅因为悲悯和爱心,我们就把大自然、把动物世界写得充满着童话般的爱意,这里面有一个真实的问题。所谓真实,是要还原大自然真实的生存状态,整个生物链的现状。
一个作家不能粉饰现实,特别是生态写作。有人可能觉得生态写作就是牧歌式的、童话式的;也有人怀着忧愤认为,生态写作就是要揭露破坏生态环境的丑恶现实,这都是片面的。我们首先要真实,而且要全面,只有真实,写出来的东西才可能有力量,有力量才能真正地打动他人,否则的话,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伪饰,偏激的揭露和轻薄的歌颂都不是大自然的本来面目。
当前很多作家随着对大自然的关注热爱,作品越来越真实,这是可喜的,但也要警惕另一种时尚的跟风的写作,防止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敷衍成篇。这是不可取的,对公民生态意识的提高以及国家整体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都没有好处。
你只有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实的世界,什么是真实的大自然,生态文学才有价值。
中国环境报:我看您的写作,并不单纯是生态内容,比如您对森林的认识,并不是一种孤独的对森林的认识,它总是跟现实世界有关系的。您是怎么做到认识与现实社会、与人产生关系的?
陈应松:我们面对的生态现实,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现实的一种。我们要探究的还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万事万物的关系。我们不能像童话作品那样构思和写作,只把最美的一部分展示出来。动物与自然之间,人与动物之间,一旦遭遇就不会是相亲相爱,而是生死对决。
森林里不是单纯的鸟语花香,动物奔跑,梦幻世界。动物之间是弱肉强食,勾心斗角,掠杀与逃命,捕食与被捕。这就是食物链的永恒真相。但也有顽强生存、顽强展示造物主给予自己的美丽,快乐,生命的尊严与大美,自然界的丰富多彩。
另外,我在写作的时候,特别是写动物的时候,我的创作经验就是写人的复杂性,写兽的人性,也就是把兽当人写。当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我想,有能力表现出人类的复杂性、兽类的人性,你的作品才可能会深刻。我自己在写作中,作品中的角色,没有人兽之分,只有长相不同。
中国环境报:当您长期在一个地方生活写作,融入其中的时候,会不会淹没在琐碎当中,分散掉写作的集中感?
陈应松:不会吧。就算是琐碎,也是美的,全靠作家的把握。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粗与细的关系,永远知道壮阔、壮丽、壮美是你毕生追求的一种写作境界,你会时时警惕自己落入琐碎和散漫。
另外,保持好奇心最重要,保持激情更重要。我每次回到神农架,就像第一次回到神农架,每次进入神农架的高山、森林、河川、峡谷的时候,都像一个小孩第一次来到花花世界一样,充满着好奇、心灵的愉悦以及新的刺激、感动,森林源源不断地给我创作的冲动,它就像我们的故乡。当你回到久违的故乡,内心肯定充满着愉悦。森林也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给你补充能量,给枯竭的、疲惫的精神和心灵补充动力,它是我的精神和写作的巨大引擎。你只要进去,就会觉得精神焕发,心中有澎湃的文字涌动,永远不会陷入惯性写作的僵硬和审美疲倦。
我特别喜欢森林,喜欢大自然,喜欢高山、大川、大峡谷,喜欢每天看到白云变幻。今天的白云绝不会是昨天看到的白云,今天的山冈也不是昨天的山冈。
中国环境报:您是如何调动自己的写作欲望的?
陈应松:别人说你的创作精力怎么这么旺盛?怎么有这么多东西要写?你基本功成名就了,可以不写了,年龄也不小了,过花甲之年,应当收手、封笔。
我从来没觉得我的年龄是一个问题,我的创作激情和表达水准是一个问题,我的作品至少语言不会出现衰老感。我感觉我的生命就是写字的,要不停地去写写写。森林和高山有太多要写的东西,而文学的内部,山重水复,我们可能只窥其皮毛,有了更多的时间,当然要更多地写作和探求。
而写作的欲望就是在森林中,在城市,我没有倾吐的欲望。每天不停地书写自然与森林,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着愉悦的过程,这种过程也是跟大自然相亲相爱、心灵交流和融合的一种方式。
中国环境报:您每天大概写多少字?
陈应松:这倒没有准,有时候写得多,写几千字,有时候可能就写几百字,也有懒惰的时候,对我来说,不多。我每天7点打开电脑,晚11点多关上电脑,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中国环境报:您写作是字斟句酌,还是一气呵成?
陈应松:写一稿时肯定一气呵成,但再后就得慢慢琢磨慢慢修改,要字斟句酌,要用最好的最准确的语言去表达,要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到极致,每一篇如此,要对自己负责,也对后来的人阅读你的作品负责。人生短暂,但文字永恒。
中国环境报:这么多年来,您始终坚持写神农架、写森林。为什么会如此坚持?
陈应松:现在看来,坚持是一种生命的福报。比如你有了一个将心安放的地方,心情和精神平缓、通融、良善、专一,没有杂念,不会走偏,更不会瞎打瞎撞、身心浮躁、移情别恋。
尤其是生态文学作家,专注写一种东西是最好的状态,不要当文学的流浪汉、万金油,就坚持写你认定的东西,不改初心,抱朴守一。因为生态文学作家所面对的比纯文学作家更难,要懂得的东西更多,更不允许你三心二意。
坚持是一种情定,更是一种傻性。但没有这种傻,你太聪明,你永远写不深入,没有高深的道法,没有安静的内心。
我爱神农架的一切,喜欢自然山野,因为它们是文学的故乡,也是文字的舞台。适合倾吐和表演,有魅力,有热量,色香味俱全。
中国环境报:作家如何在写作中体现自己的思想和内核?
陈应松:还是先要划定一个地方,你才能思考和书写,真的不要太多,不要到处思考世界。这个世界太大,你思考一点地方就行了,思考几种动物就行了,何必要把自己弄得很芜杂、很博学、很丰富、很有见解?农林商,文史哲,说天天知道,说地知一半,这样的人是百度,不是作家。
我的办法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山外的事与我无关,我山里的事还没弄明白。作家的思想是随着你的题材处理走的,不可主题先行,一切,都得由着你钟情的题材而来。思想、主题,都是你反复思索过后的东西。不要循着某种暗示去写作,不要带着主题去写作,不要生造思想,不要处处思想。什么都要插一杠子,什么都有感慨,都可以侃侃而谈、长篇大论,你就成了写作油条和意见大王,你不是作家,也不可能有独到的见解。
对一个生态作家来说,他不能干记者要干的事,作家要更加细腻地表现生活的丰富性,表现人性与兽性的复杂性。
作家写作的文字是精神世界的外化。比方说,你写一个虚伪的、虚假的、肤浅的动物世界,一读我知道你对动物世界根本没有爱,没有悲悯,你不懂动物所处的环境,你完全凭借你的想象,想当然地迎合读者和出版的趣味,或者说你自己根本就不努力写作,人云亦云而已。
这样的作品大量充斥在我们中间,不仅仅局限于生态作家,很多作家都是如此。为什么说生活非常重要呢?巴尔扎克说,生活是第一位的,生活永远是最重要的。无论你有多高的才华。何况现在很多作家的才华和文字表达的功力是有限的,如果不靠生活去弥补,只会更加糟糕,捉襟见肘,表达破绽百出,让人轻看。
作家要有出息,就得老老实实到某一个地方,好好地待下去,沉浸下去。
难道梭罗是为了写《瓦尔登湖》才到那去的吗?他是到那儿去生活的,首先是生活,生活是第一位的,写作是次要的,是生活副产品。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也不是为了去表达而写作,这都是本末倒置的写作态度,值得警惕。
今天生态写作虽然方兴未艾,但我还是呼吁,作家要好好地沉下去,好好地去感受大自然、体会大自然、触摸大自然,才能热爱大自然、悲悯大自然、书写大自然。
中国环境报:您觉得哪个题材的生态文学作品会更有影响力?
陈应松:题材不分大小,写好了都是大题材,写坏了都是小题材。虽然生态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地球的未来,是大题材,但处理得不好,就是微不足道的小题材。
我喜欢写大兽,但实话说,你写一头猛兽跟写一个病毒,在题材上面,它的意义是同等的。问题是要把它写好,写出大气象、大境界、大手笔,就很难。
一个人写老虎,未必他就能成为一只文坛的老虎,写蚂蚁,他就是文坛的一只蚂蚁。坎布尔写《昆虫记》,一样成为伟大的作家,这种例子太多了。
中国环境报:您每次进山、进森林是什么状态?观察,记录,还是用耳朵听,用眼睛看?
陈应松: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我大量的风景描写实际上来源于我的日记。早上起来,我要听是什么鸟在叫,山上是什么情况,天空是什么样子,气候,植被,我都爱仔细地观察,然后像一个画家写生一样,用文字记录下来,这是我的一个良好的习惯。
一个生态作家,本身就是面对大自然的,你会有永远学不完的知识,在山里不懂就问,山民是最好的老师。我家里动植物的书也有一大堆,还有当地历史的、人文的、风俗的、科学考察的,各种各样的书。
很老的书我也要,孔夫子旧书网上,不管多贵,我都把它买下来。那里面有我许多想要的东西。写神农架,要懂神农架,写什么,像什么,与其说是一种本事,不如说是一种科学态度。生态就是科学,所以,我自己认为我是关于神农架的半个植物学者、半个动物学者、半个地质学者、半个民俗学者、半个历史学者。
中国环境报:您每天都写日记吗?
陈应松: 写日记是我挂职时每天的工作,现在的一些灵感、好句子,风景描写,则写在手机上面,但不一定每天。有些稍纵即逝的感受一定要记下来,否则就忘记了。
很多人说你怎么这么能写?我都是积少成多、平时积累的,不是突然去写什么,没有那么多东西。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没有谁有这么好的记忆力,更何况我们是专业作家,一定不能偷懒,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写作,就像农民那样好好耕耘自己的土地。农民说,一年不种一年穷,我要说,一天不写一天穷。穷是说你就过气了,不算是作家了。
中国环境报:行走之于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陈应松:一个作家,必须要有游历的兴趣,要走遍名山大川,心中才有壮阔气象,局限待在某一个地方,视野难免太狭窄。
我除了待在神农架,也不会放过任何出游采风的机会,所以我去了祖国东西南北的大量地方,这对于写作是极好的营养。作家要不停地行走,人就应该是一株行走的植物,通过行走汲取大地的各种营养,山河是我们身体的必须。
一个好的生态作家,他肯定是靠山川河流的滋养和熏陶造成的,大自然是滋养你的,你再用文字来反哺大自然。
一个作家,通过脚步的丈量来拓宽自己的视野和精神的疆域,你的笔力是靠山河的钙质支撑的。
中国环境报:您今后有哪些写作计划?
陈应松:我心中已经成熟的至少还有三部长篇。我现在居住的地方离森林就只有十几米,每天晚上能听到森林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野兽叫声,我每天晚上打羽毛球,旁边就是山坡,我有时生怕山上会冲下来一头狗熊。写作就是跟这些想法一样,有突然性,我的写作规划不是很缜密,有随意性,但我不会不写。
我的写作总是离不开神农架,我此生卖给了她,当然,这是必然的选择。我可能也要写写江汉平原,我的家乡。总之,我会写下去,如果我不写作,我的生命就结束了。上苍派我来人世就是写字的,写作跟我的呼吸融为了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