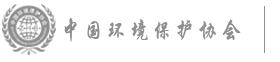刘泽军,法学教授,曾受聘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法治政府建设”督察组专家成员,现为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特聘法学专家、北京市石景山区法律顾问,现任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和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表明,近30年来新出现的约75%的人类疾病是人畜共患,其中多源于或通过野生动物传播。
目前,小小的新冠病毒已给亿万人的生活带来极大冲击,但其野生动物宿主和中间宿主迄今仍未最终确认,不可预见性给疫情防控带来很大的挑战。
当前,我国抗“疫”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国外的形势仍不容乐观。那么,针对突发事件,我国构建了怎样的监测预警体系?在疫情中又存在哪些挑战和短板?应从哪些方面予以补齐?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刘泽军教授。
“预防为主”是重大疫情防控法律制度体系的基本原则
最具挑战性的两大因素:监测和预警
中国环境报:作为一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可预见性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您能否介绍一下我国现行防控体系基本情况?
刘泽军:我国现行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大多基于2003年SARS疫情后构建的。
在立法层面,12部基础性法律与11部关联性法律、14部行政法规、21部规章相继出台、修订、修正,再加上其他辅助性规章,基本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框架,涵盖了统筹部署、疫情防控、应急管理、卫生医疗、人员管理、市场监管、交通旅游、海关检疫、财政保障、公益慈善、基层管理、劳动保护、法律责任等13个领域,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起到了规范指引作用。
特别是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为立法主干所构建的疫情防控制度,具备了体系化的特征。
本次疫情暴发后的紧急处置,也基本上没有脱离以上法律规范的指引。
中国环境报:疫情初始,我国部分地区也曾“手忙脚乱”,随着防控的深入推进,全国治“疫”才有了当前战果。通过此次疫情事件,您认为在处置突发事件方面我们还存在哪些挑战?
刘泽军:疫情防控本身是“防”与“控”两个阶段的统一体,也是一个 “预防”+“控制”的完备规则体系。
对于“防”,重大疫情防控法律制度体系的基本原则都确定了“预防为主”原则,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监测和预警两大因素。在“控”方面,我们在此次战“疫”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疫情蔓延得到有效控制。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政府主导的网格化信息监测发现制度,涵盖了监测项目、监测点、监测区域、监测信息库、监测设施建设、专兼职人员配备等内容,在此次疫情监测中也达到了预期:发现了不可知、不确定的新冠病毒,并在一定程度上熟悉了解了病患症状,为工作进一步开展打下基础。
但从监测体系角度来看,这还是不够的。
监测体系包括信息监测发现与会商评估两个部分。这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设计中有充分体现,它们共同构成了突发事件应对决策所依托的专业性判断的基础。
在监测发现之后应该如何处置,也就是对于具有科学、专业属性的监测结果如何处置的问题,是会商评估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它更直接影响下一阶段的预警决策。
从这次疫情过程来看,会商评估在时间节点上的滞后一度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监测体系的构建以纯粹的科学追求作为唯一的品性,从而形成突发事件应对决策的基础要素,无论是信息监测发现还是会商评估,都应坚持这一根本要求。
尤其是在涉及科学专业判断的基础环节设计上,必须遵循这一原则,与此相关人员应被赋予“直通车”式的信息传达,不能出现科学、专业信息被“滞留”的情形。
对“预警决策”的理解有误:“预警决策”不是疫情信息公布。法律上规定了“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及时、准确”,二者本质上有着根本差别。从监测、预警的预防阶段,到应急响应、处置、治理的控制阶段,是紧密衔接但又各自独立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预警决策、四个级别预警的设计以及相应的预警措施的规定,都属于“预防”阶段的应急处理。只有这个时间窗口内发生的的疫情还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时,才会有作为预防阶段终结的“疫情信息发布”。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一个新的时间窗口才会打开——疫情控制。
监测与预警是一种具有专业属性的行政行为
核心在于发现问题,核心理念支撑是法治
中国环境报:如何正确理解监测预警的属性特征?
刘泽军:监测与预警是一种具有专业属性的行政行为,其核心在于发现问题。
在疫情防控法律制度的设计中,这种发现应该被赋予更为特殊的涵义。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虽然已经跨越了“传送带”模式的狭隘,同时也超越了依赖“专家模式”可能产生的“固执”,走向了一种更强调多方“利益代表”的模式,强调一种“合作与治理”状态的认可。这种“合作”就是对“专业行为”的行政法认可,这种认可是一种授权,一种可以借助专业评判,拥有更多优先属性,甚至拥有“责任豁免”资格的公共利益实现行为。
此外,从现在关于本次疫情监测与预警的信息披露来看,在很多方面与现行规则的法律行为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现行规则可能会有基于专业认识的更为细致的设计,但无论怎样的专业,作为一种行为类型,一种应该被赋予生命保障之源重大使命的行政行为,其核心的理念支撑就是法治。
中国环境报:针对预警主体,《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都分别做出规定,是否存在冲突?
刘泽军:《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3条规定,“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明确“预警决策”的主体是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同时作为行政法规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又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提供的监测信息,按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发展规律和特点,及时分析其对公众身心健康的危害程度、可能的发展趋势,及时做出预警”,明确“预警决策”主体是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应该明确的是,二者的规定并不冲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的“做出预警”是预警式报告,为政府“快速反应”和“预警决策”提供专业判断的依据。
同时在上位法的预警决策机制设计中,政府最终的预警发布,就是建立在卫生部门、监测机构的科学判断的基础之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决策具有风险决策特性
“风险评估”作用应更凸显,其结果应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
中国环境报: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您有哪方面的意见建议?
刘泽军:进一步完善基础性法律的规范。《传染病防治法》虽有“发出预警”的原则规定,但之后的条款不够细化,仅在“传染病预防”一章中概括提及了国家与省级政府发布预警、地方政府制定预案的规定。
同时,通过《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3条可以看出,预警决策与上报应当是同时的,并对时间节点和决策方式(报告、越级上报、通告)进行了规定,实际已有了“预警决策”的明确授权。
《突发事件应对法》是为了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而设计的,在适用效力上低于《传染病防治法》。
但《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时间(2007年)又晚于《突发事件应对法》(1989年施行,2004和2013年分别修正),因此从特别法的时间效力上看,应该适用于《突发事件应对法》(新法)。这就很大程度上存在一个问题,譬如此次疫情的“预警决策”具体应该适用哪部法律?
“风险”应成为立法完备的基础理念。《传染病防治法》全文13247个字,没有一处出现“风险”字样;《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全文9887个字,也只有6处出现“风险”字样,且其中的4处还是保险风险、救援人员风险(在控制阶段的)结合在一起的。
虽然出现“风险”字样的次数,并不能代表立法者对风险认知程度的多寡。但不能不说,也反映了这两部基础性法律在立法起草时的关注点——基于抗击SARS成功经验模式的提炼与总结,对“风险”认知和重视程度不够。
因此,在理念、原则、方案、措施等方面,对现行制度体系进行逐条检视、关联检视势在必行。特别是对“风险”的重视、对“风险治理”的推崇,应该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要成为立法完备的基础理念。
“风险评估”应在行政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2019年出台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规定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等重要程序规则,并明确要求“风险评估结果应当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
但在法治政府建设推进的过程中,本人依托对地方政府实践的长期观察与调研,对政府决策中的“风险评估”环节深有感触:部分重大事项决策中的“风险评估”环节更多体现为“锦上添花”。
突发公共事件的预警决策更具有风险决策的特性。风险决策不同于一般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应更为凸显。
我认为,在风险社会条件下,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行政决策——“预警决策”应该在一个更大的治理格局中找到法治品性的合理定位。